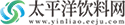文/陈桥生
一
仿佛一艘巨轮,穿越2500年的岁月长河,静静停靠在三湾古运河畔。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2021年6月16日,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。这是一座百科全书式建筑,全流域、全时段、全方位展现了中国大运河的历史、文化、生态以及科技面貌。
穿过午后的阳光,我们走进这座巨轮造型的博物馆。扑面而来的,是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一段河道的横断剖面,将人瞬间裹挟进幽邃无边的时间深处。这段河道,取自河南开封州桥及汴河遗址,剖面从下而上,分别是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地层,由左向右,则是一条条蜿蜒的白线,标示出不同年代汴河河床的走向。
最底端的唐代河道地层,触手可及,其白线呈现“锅底”形,可见当时汴河河道深且广。不难想象,其时的汴河上,舟楫往来,络绎不绝,是如何的繁盛。而此后历代,随着汴河地位下降,河沙逐渐淤积,汴河河道变窄变浅。到了清代,曾经繁盛的汴河竟成了“小水沟”,而今则完全淤平为陆地。
一眼千年。一条运河在千年时光中的流转与变迁尽在眼前。剖面上密布的大小颗粒,有砖瓦、陶瓷,有动物骨骼,有金属类生产工具,它们因何而来,为何在此,又蕴藏着怎样的前尘往事、因缘巧合,令人浮想联翩。
沧海桑田,历史的年轮仍然以地层的形式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大运河,以如此惊人的空间和时间尺度,展示着它非凡的价值。
从博物馆出来,已是夕阳西下,我们在门前公园的草坪上席地憩息。夕阳的余晖,顺势将我们包融在万道霞光中。同行者举起手机拍照,引来更多人的加入,最后一位进来的,情急之下,玉体一横,直接侧躺在众人前的草地上。这曼妙的一陈,不期然竟妖娆出运河的形状,瞬间将大伙的情绪点燃,嬉笑杂糅着阳光,洒满一地。
二
眼前的三湾湿地,满目翠绿,白鹭翔集,不断延伸的塑胶跑道两旁,散布着樱花,琼花,香泡,香樟,香柳,微风徐来,花香鸟语,令人神清气爽。
扬州三湾,是整条运河中最古老的一段。公元前486年,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,以水路沟通江淮,在此挖下修凿邗沟的第一锹土,大运河便有了起始河段。扬州,也因此成为中国大运河的“生长原点”。
逝波千年,千里运河如同在扬州歇了歇脚,拐了几道弯,河道蜿蜒,静水流深,涵养了今日独特的三湾风光。
三湾的形成,缘于明代扬州知府郭光复。
扬州城自古北高南低,运河旱季水势直泻长江,水位过低,漕船、盐船常常因而搁浅。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,时任扬州知府郭光复,舍直改弯,增加河道长度和曲折度,以抬高水位,减缓水的流速,将原有百余米直行河道,曲折圆转成1.7公里的河湾。水流舒缓了,通航顺畅,形成了“三湾抵一坝”的奇观,进而吸引更多的文人商客,骑鹤下扬州,于此舍舟登岸。
不同于天然河流,运河是人的创造,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。一条运河,荡涤着半部华夏文明史。流水汤汤,千年不辍。置身世界遗产名录,却是一带活泼泼的水,始终流淌在寻常百姓的日子里。
三
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!今天,行走在大运河畔,更多的已非“寻古”而是“叹今”。一路北上,俯瞰船闸,漫步大堤,面对种种水利奇迹,处处都能感受到中华民族那种艰苦奋斗、开拓进取、生生不息的精神。
抵达镇江谏壁船闸,恰好遇上一天中运河与长江水位齐平的时刻。无须开闸放闸和等待通行,现代版的“舳舻转粟三千里”在眼前生动演绎。船闸仿佛一个巨大的、具象的枢纽开关,对“十字水道”上的繁忙交通进行自如地开合切换,让自然的水安服于人类的需求,让南北百货在此有序地交汇融通。
站在岸上,能清晰地看到船民们的忙碌生活,男人在驾驶舱里操作,女人则在甲板上忙着家务,甚至侍弄着盆栽花草,这是他们流动的家,是全部的希望,是千百年来不变的日常,似远犹近。
一条不宽的水道,却能让他们满载货物的千吨级船舶从其间驶过,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大运河依然生动地“活”着,并且活力如此强盛。
在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,我们寻访到了西津渡——长江、运河交汇处的古渡口。这里是唐代张祜写下“两三星火是瓜洲”的金陵渡,是宋代王安石写《泊船瓜洲》时深情回望的“京口”地。
夜访西津渡,在长约千米的古街轴线上,保存至今的元代昭关石塔、古救生会、待渡亭……依次而来,历史的厚重被一次次掀开,多少繁华如电影镜头般在我们眼前一幕幕浮现。
由东往西走,从高往下看,人如海,灯如昼,仿佛便是行走在舟楫交织、人声鼎沸的历史街市,饕餮着千年古渡里朴实平凡的“人间烟火”。
京口瓜洲一水间,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想起多年前的某个日子,曾经逆向而行,专程从西津渡折返,去对岸扬州找寻那两三星火的瓜洲古渡。
导航当时迷失在一片滩涂之中,问寻之下,路人纷纷指向前方繁忙运营中的瓜洲渡口。我们说找的是不再使用的渡口,弄得人家一脸茫然,不再使用了,你们还找去干嘛?好在最终得偿所愿,在芳草萋萋的水中小洲,找着了写有“瓜洲古渡”四个大字的一块竖碑,据说古渡头就湮没于其下。不远处还附会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“沉箱亭”。
一水相隔的京口、瓜洲,多少伫视回望,多少明月相照,演绎着多少悲欢离合。那首“孤篇盖全唐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,据考证,描写的就是以瓜洲为地标的长江春夜景致。
不知江月待何人,但见长江送流水。
四
运河的一头系着江淮和江南,另一头系着京都,京都的变迁,决定了运河的变迁。隋唐运河以洛阳为中心,北至涿郡(今北京),南接淮水,贯通长江;北宋定都开封,通济渠依旧发达,但从洛阳通往北京的永济渠就衰落了;南宋定都杭州,开封到淮河的汴河开始淤塞,扬州、淮安的地位下降,苏州成为运河沿线最重要的城市;元代定都北京,必须新开河道,截弯取直便形成了京杭大运河。
或截弯取直,或舍直改弯,运河的每一次蜿蜒转向,缘于自然的造化,更标示着文明历史的走向。上善若水,水利万物而不争。纵贯起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的运河,它的雄心已不止于江淮两岸,更远及于南方之南。
一如精于“打劫”的围棋手,隋炀帝在动用百万民众疏浚大运河之时,应该就已经瞄定了广州“南海神庙”,这是他的父亲早早就为他在南方之南备好的一着先手棋。
在反复的开劫应劫下,历史的天平向着南海倾斜。
唐中期以后,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受阻衰落,以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,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从西域转移到了南海。
历史一转身,便凸显出岭南通往江淮、长安的交通瓶颈。由于隋唐大运河的贯通,再溯长江、赣水而上,便可直抵大庾岭北麓,越大庾岭顺北江而达广州,通往海外。此中,最艰难的关隘,即是横亘其间的大庾岭路。
其时的大庾岭路,无法车行,只能是肩扛人背,所谓“以载则曾不容轨,以运则负之以背”,远远无法满足“海外诸国,日以通商”的通行需求,无法将海外通商之大量货物,转运至江淮等地或朝廷府库之用。
这个历史的机遇,恰逢其时地落在了身为韶州人的张九龄肩上。
五
唐开元四年(716)秋,张九龄奉命开凿大庾岭路,次年即大功告成,辟通为“坦坦而方五轨,阗阗而走四通”的大路。因修路有功,张九龄由八品官升七品,算是一个应得的奖赏。
然而,其功之大,却是如何形容都不为过的。张九龄打通的,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要衢通道,更是帝国的经济命脉,是连接海洋通向世界的最重要关节,是贯通古与今、中与外、陆与海的海上贸易之路的任督二脉。
打通了任督二脉的南北交通线,就像在中华大地画下的一个巨大惊叹号。饱蘸运河水,汇聚全部奔腾的伟力,以不可阻挡的气势,冲决逶迤横亘的五岭,在南海边圈定惊叹号最后的那个圆点。
张九龄一定是感受到了这份磅礴的伟力,澎湃着大海的激情,且行且吟且唱着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的千古绝唱。
因为大庾岭路的开通,天涯共此时,不仅在现实中成为可能,更是站在历史交汇点上的张九龄,也是岭南,向世界发出的最早的时代宣言。
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。如果说此前的岭南,面对的是一片茫茫大海,从此海上便生起了一轮明月。有了这一轮明月的普照运行,岭南的天空不再暗黑,这片大海也因此而波光粼粼,气韵生动。
(更多新闻资讯,请关注羊城派 pai.ycwb.com)
来源 | 羊城晚报·羊城派责编 | 吴小攀 易芝娜校对 | 谢志忠